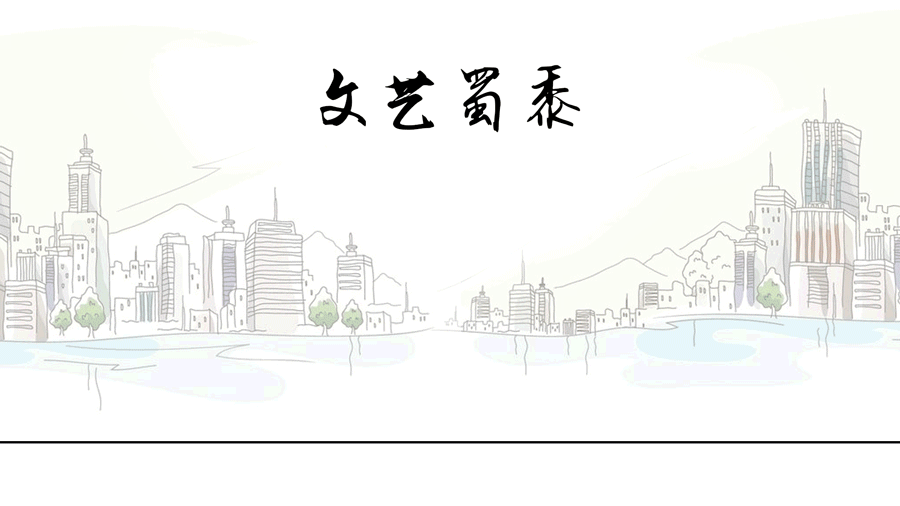
站在中路藏寨的观景台上,一位裹着绛红藏袍的阿妈指着山谷对我说:今年的花比往年开得疯。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片山坡上的梨树枝干上挤满了密密匝匝的花,远处的墨尔多神山沉默地托着蓝天,碉楼的尖顶闪着光芒,几只山鹰盘旋而过,这就是丹巴的春天,美得忘乎所以。

中国赏花地那么多,为何丹巴的梨花让人念念不忘?是百年古树的沧桑?是藏地风情的厚重?还是那雪山、碉楼、经幡与花海碰撞出的极致浪漫?

十年前我第一次来丹巴时,以为这不过是又一处“网红打卡地”,直到在梭坡乡遇见一株300岁的梨树——它的根紧紧抓着悬崖边的岩石,花开得比山下更烈,像在向雪山证明生命的倔强。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丹巴的梨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自然与人文的对话。

在甲居藏寨,记得扎西大哥爬上屋顶指着外墙的日月图腾说:“我们嘉绒藏族盖房子,石头缝里要撒青稞,房梁上要刻莲花。梨树种在梯田边、碉楼下,花开时护着寨子,结果时喂饱山雀。

在丹巴,我见到好几次夕阳把最后一道金光打在古碉残墙上,一树梨花被映成半透明的水红色,穿藏袍的老阿爸赶着牦牛从花影里走过,牛铃叮当好像惊起一片花瓣雨。

那时候跟着一群摄影师在日出前半小时去‘日落观景台’,逆光拍花海里的炊烟;中午到巴底乡拍梨花撞上油菜花的黄白交响;雨天也不犯懒,带长焦冲进梭坡古碉群,雨雾里的梨花像蒙了层唐卡的矿物颜料似的好看。

丹巴人把春天的梨花做成了美食,藏式火锅里飘着酥炸梨花天妇罗,咬开脆壳,花瓣的微苦回甘让人想起山野的气息;我还尝到过村民自酿的梨花蜂蜜酸奶,勺底沉着去年晒干的雪梨片;最惊艳的是梨花炖藏鸡,汤色清亮,缀着嫩黄的花蕊。

上一次离开丹巴那天,卓玛塞给我一包梨花标本。车转过第五个山弯时,手机突然震动——是扎西大哥发来的视频:昨夜那场大风雪后,朝阳正从墨尔多神山后升起,被冰晶包裹的梨花折射出七彩光晕。他粗粝的嗓音带着笑:“明年花开时,记得带故事回来。”我突然红了眼眶。原来在丹巴,比梨花更珍贵的,是这群把日子过成诗的人。所以我断定,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再来,在好多个梨花盛开的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