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陈宏谋认为“天良”是值得珍视的古代遗产,但他担心这笔遗产失去魅力,为人忽略,所以采取上述努力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他对“人情”观念的推重有着不同的含义。在陈宏谋的时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情”或“人情”这个问题如此兴致勃勃。
他对这个概念的关注大部分旨在缩小这个词语的内涵,因为该词语当时有种种解释,他为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目的而捍卫这个概念。
对“情”或“人情”含义的争论是清代早期特有的文化现象,陈宏谋作为这场争论的积极参加者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属于清代早期的人物。
“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词语,《易经》中已经广泛地使用这个概念,有"环境"、"真诚"、"现实"、"喜爱"、"欲望"等不同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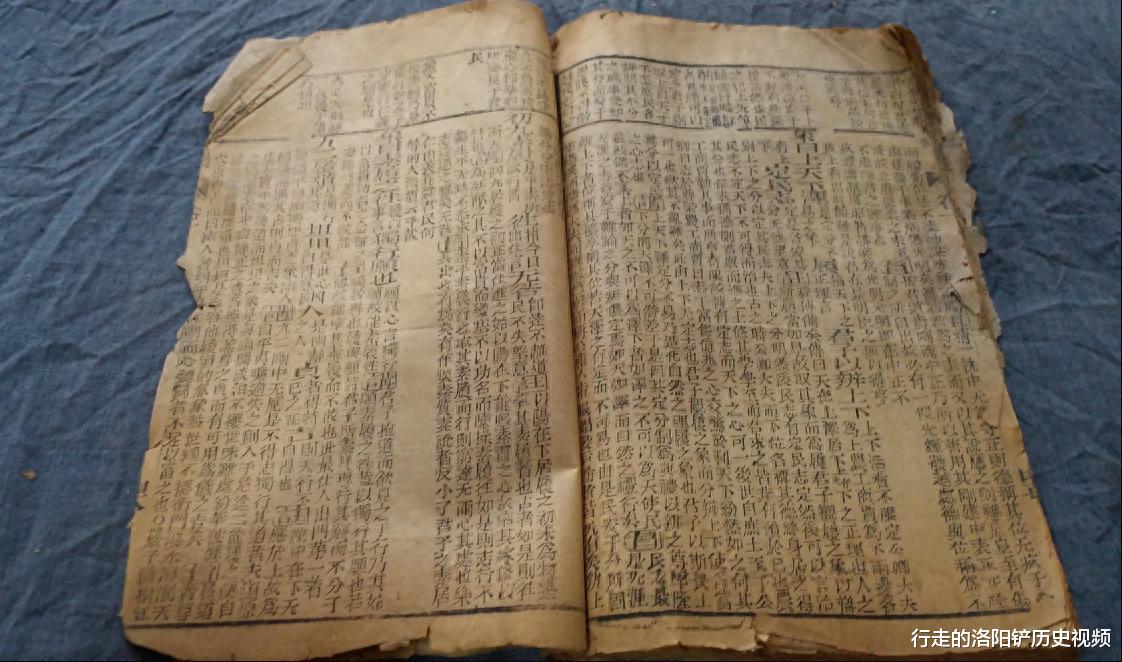
在古典文本中,它经常成为"七情"的缩写,即喜、惧、怒等七种情感。“人情”经常(但并不是全部)和“情”同义或缩写为"情",它在汉代《礼记》中指的是子女和家庭情感的纽带。
帝制后期"人类情感"的意义可延伸为"同感"、"互相的责任"、“爱情”、“赏识”、“共同的态度”,甚至是“舆论”等不同概念。
明朝晚期到清朝中期这两个词语的语义共同经历了剧烈演变,意义扩大并引起了争论。
与所有为情辩护的观点(虽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加以掩饰)相对立的是宋朝的理学传统,虽然该传统没有谴责人类情感,但毫无疑问,它倾向于通过一系列实体论的方法把情和理、人性分离开来,认为情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有害和诱使堕落的作用。
例如程颐写道:“心本善,发于思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
根据朱熹的观点,性是所有人共同的,并与理相一致,而情随个人性格而异,个人性格同人类共同的本质完全不同。朱熹补充道:爱恨皆情,然而爱善憎恶却是性的一部分。
情和性(或者情和理)的二元论以及在道德上对情感极度不信任是随后几个世纪风行的宋朝新儒学思想遗产的关键部分,而宋儒对性情之间的复杂关联的重视为后来的信徒忽略了。
恰恰是这种二元论和对情的消极观点在近代早期社会受到了彻底的挑战。

读者将会留意到在明末清初,像上述的例子中提到的,“情”的每个不同用法都包含了积极的含义,这也包括了《牡丹亭》里的激进用法,在这本书里"情"被视为抵制和战胜了"理",而"理"被理解为因循守旧的道德伦理。
后来各个流派的新儒学思想家,从相对反传统的何心隐、李贽到正统的(虽然带有其自身的创新)吕坤、颜元、钱大昕和戴震都参与了为人类情感恢复名誉的集体文化工程。
同时,在迅速发展的平民文化出版物里,情的广泛流行引人瞩目,甚至成了一种膜拜。
在那个时代充满浪漫色彩和色情的大众化小说里,在流行的诗集中(日益以女诗人为代表的诗集),情作为浪漫的爱情和强烈的情感成为中心主题。
正如明末一位文人所说:情是生命的全部!明末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陈子龙在其著作中对情感具有全新的评价,他把理想化的爱情与英雄般地效忠朝廷的情联系起来,从日常的经历中提炼出了美德和忠诚。
情,不是对人天生善良的腐化,而是对高尚道德的凝结。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语境中,"情"和"人情"这两个习语占据了陈宏谋思想和话语的中心地位。

最重要的是,他高度强调和始终如一地坚持一点:不论是本体论还是伦理道德,都没有将情和理二者截然分开。二者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在陈看来,他的感情政策应包含人情和天理两方面;他用四个字的习语将情和理联系起来,例如"合情合理"或"通情达理"。
他经常简单地把这两个词合并为一个词,"情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近代早期对“情”的理解,与程朱理学的观点针锋相对,但陈宏谋却不这样认为。
不过,他从不引用宋代作者对此问题的阐述,而是视自己为程朱理学传统正统的代言人,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已经反映了程朱理学。
然而陈至少在一个场合暗示,人情和天理的二元论是后来对传统经典原意的曲解。但是如果宋朝的道德哲学家总是把理和情对立起来,那么陈那个年代的通俗文学也是如此。
差别在于哲学家认为理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文学作品中情战胜了一切。陈宏谋对人情的复兴,将人情与天理等同起来,这可以被视为同时反对两种主张——道德理想主义者及浪漫主义者的主张。
尤其是,由于人情和天理不能区别开来,人情成为陈宏谋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例如,他详述了一些虐待他人的常见形式,并在每个事例后询问读者:
这种行为跟人情真正相符吗?他认为能被一般人所接受的恰当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人类情感的标准"("准于人情")。

人情为人际关系中的互惠(“恕”),为与他人产生同感(“体人”),为他人承担责任(“责人")和教育他人("教人")的个人能力都提供了基础。
只要把尊重人情的原则在逻辑上稍微引申一下,就能找到适当的治国安民之策。学术官僚们常担负着论古以治今的使命,但这一使命只有符合人情才会被完成。
陈认为“王道本乎人情”。但是在陈的用法里"人情"的精确含义是什么呢?首先,他使用的这个词显然不只有一个意义。
例如,当他用"不老实"来描述湖南的人情时,他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当地流行的习俗,而非任何超常的现象。
陈也把“人情”延伸用来说明某些我们可翻译为“公共舆论”的内容。尽管这些词的交叉使用耐人寻味(他用描述人类感情和理性的术语去描述"公共舆论",用这种方式赋予“公共舆论”一种在其他语境中不具有的魅力),但在这里它不是我们直接关注的。
我们所关注的是陈在他那个时代里使用这个广为流行的词语的方式,并声称是自己独特的方式——缩小词语的内涵并赋予道德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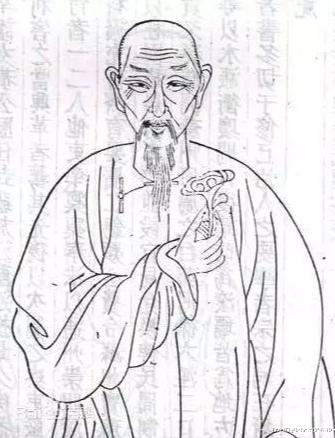
陈宏谋对人情的理解包含了人类理性和人类的情感,二者在道德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但几乎不轻易引起或表现出来(汤显祖把情作为一种强烈的感情,肯定是与陈的用法格格不入的)。
人情每一点都跟天理一样,是“自然”的。与理相同的是,情呈现出了“规律性”或固定的、可预计的运作规则(“情理之常”),它与理一样,是不可“亵渎的”(“不可非”)。
个人考虑行动的步骤或政府制定政策都不能忽视或压制情。这样它对政治行动进行了有效的限制:
例如,一项对百姓有过分要求的政策是与人情相违背的,因而是无法操作的,也是不合乎道德的。
陈当然也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制定的政策并不总是与人情相互协调的。例如,他引用了一些社会精英的剥削行为的例子,这些例子很明显与人情背道而驰,却不被法律所禁止。
因而,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与这些人的行为做斗争。情/人情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市场行为中表现得最为清晰,这里政策的含义意义非常重大。
商人们按对自己有利的价格买卖商品无非体现了他内在理性对市场供需条件的反映,这类行为既合情又合理,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一点,允许商人按市场供求关系从事交易。
但是人情不仅是理性的简单运算,同时还是爱或同情(“体恤”)。
最明显的例子是生活在中式家庭里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出于(陈认为普遍是正确的)人情的冲动,因为它显示出对家人自然和理性的情感。

人情是一种同感,它对一个人所期待的大众行为加以约束,正如人情是一种市场运行一样。
例如,陈认为,忽略人们对礼仪的普遍看法,敦促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礼仪规范,这本身就构成“过礼”的行为。
由于我们全都分享了这种人情,当仪式上的要求不太适宜时,我们能通过自我检查,通过我们自身苦难和忧患经历的积累来确立正确的行为规范。
对陈宏谋的人情观影响最大的是明末经世思想家吕坤。陈宏谋在注解吕坤的著作时,提出一个过去学者们未深入讨论但对人类情感的真正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人情和自我利益的关系如何?陈认为宣称公共利益(“公”)与人情完全相等是天真的,只讲对了一半。
实际上,人类情感既包含公共意志的因素也包含私利的因素(“人情有公,亦有私”)。就整体而言,私情是真实的,是内在的人情;严格说来,它们不能也不应该被压制和忽视。
陈运用许多策略试图使私情和人类情感的全部含义相吻合。他当时阐述说,虽然作为一般现象的人情是一种公共情绪,一旦降低个人行为(“个做”)的层次,它们就变得只关注自我。

在其他地方他把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表达天理,另一部分反映个人利益;他进一步坚持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的"。
他还把人情分为三部分:自然和直觉的部分("自然")、个人必须去做的部分(“当然”)和个人不能回避的部分(“不得不然”)。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偏袒自己和接近自己的感情是理性的、合法的,并防止他们过分沉迷于自我。
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模糊的,这是他思考过程中真实想法的反映,他没有得出使自己完全满意的解决办法。
人们必须受到自己内在原则标准的指导(“准之于理”),关键是要保持同情心,能一直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思考("体他")。
总的来说,陈对社会进程很有信心;通过社会各界相互之间不断地协商,在实践中可以达到利己和利人的平衡。
最终,陈也回到了对人们尊重秩序和先后次序的信任。他引用了吕坤关于市镇交通流动的一个奇怪而乐观的隐喻:

当人们在街道上相遇时,男士让路给女士,骑马者让路给步行者,行动灵活的人让路给行动迟缓的人,年轻人恭敬地让路给年长者。
在吕这个理想化的街道场景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他是如何把正统的儒家顺从的例子(年轻人屈从于年长者)和无疑是非儒家的谦让的例子(男士让步给女士)并列对照,以及如何把坚强的给弱者让步的例子和与其相反的例子并列对照。
在这个意义上人情简单地显示出物理——统治实际生活的原则,即"人们无需法律强制就能自觉遵守的"原则。
陈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没有比利用这些根深蒂固、自然的秩序观念为指导更好的方法了。
陈宏谋提出的关于自利这个哲学问题的各种答案(可能除了最后一个)都是传统的,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对问题的关注本身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某种程度上,陈只是参与了余国藩所说的围绕个人欲望问题所展开的“哲学与诗词之间的争论",哲学家们坚持认为情要为道德和社会所接纳,必须合乎逻辑并受到风俗习惯的节制(“节”);正如余国藩指出的那样,这场争论至少早在荀子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更为特殊的是,陈宏谋反复强调,人类欲望是合法的,是不可压抑的。
他同中国近代早期的其他思想家为自利(“私”)和个人好处(“利”)这些观念平反,把它们从宋朝理学传统强加于他们的幼稚、简单、肤浅的责难中拯救出来。
陈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将个人的重要性向前提高到了与集体主义相等同的一个崭新的意义,这对当时思想和政策的演变有着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