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9日傍晚6点,北京街头,一位62岁的医生骑着自行车穿过红绿灯。

没有人想到就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在普通得画面,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失控的汽车从侧面撞来,抢救一天一夜后,这位医生最终离世。

他是修波,我国脊髓神经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是无数脊柱裂患儿口中的“修爷爷” 。
他的离世让医学界和患者群体感到意外又悲痛。

去世前一个月,他刚被北京航空总医院聘为神经外科特聘专家,62岁的他仍保持着每周十余台手术的工作节奏。

同事回忆,他常忙到凌晨才回家,睡三四个小时又回到医院,甚至车祸当天,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还在更新科普视频——那是助理按他提前安排发布的最后一条动态 。

专业领域,修医生是“中国神经管畸形治疗第一人”。
他创建了国内首个神经管畸形诊治中心,完成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脊髓栓系综合征显微手术,曾让一名被遗弃的脊柱裂患儿重新站立。

“他做手术时,会握着孩子的手轻声安慰,仿佛那不是一场手术,而是一抹希望。”

修波的职业生涯始于1982年。
那个年代,脊柱裂患儿常被贴上“终身残疾”的标签,许多家庭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选择放弃。他曾在山西义诊时,为一名弃婴免费手术。

术后孩子养父母跪地痛哭的场景,让他更坚定推动公益诊疗。43年间,他参与十余次完全自费的偏远地区义诊,连交通食宿都坚持自己承担 。

他的学生记得,修波总在实验室待到深夜,桌上摆着脊柱模型和显微镜。
“脊髓神经比头发丝还细,差一毫米都可能瘫痪。”他说,医生手里握着的是一个人能否体面活着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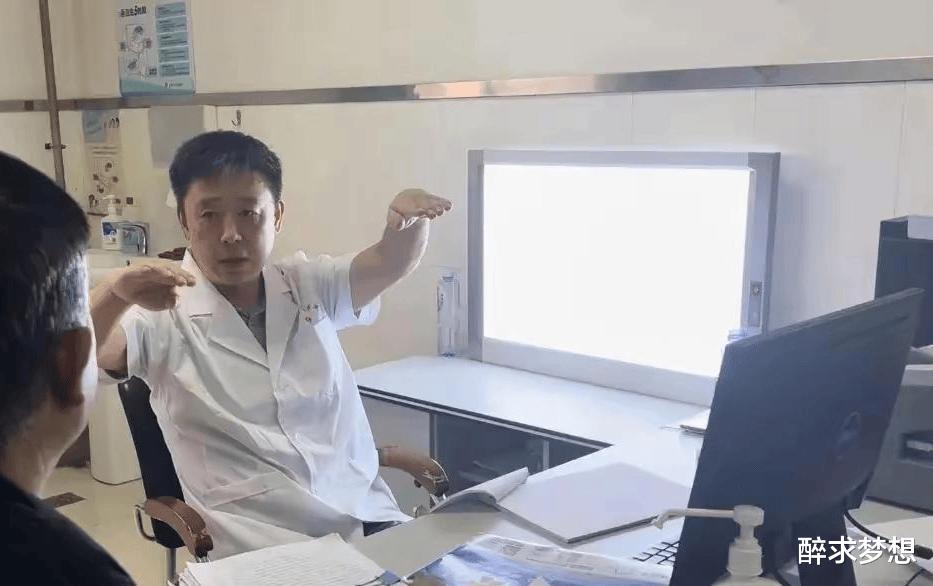
令人不得不遐想的是修波并非近年唯一因车祸离世的顶尖学者。

2024年,空间物理学家张效信死于货车撞击;2023年,38岁的军事智能专家冯旸赫在网约车事故中当场遇难;


同年,转基因安全专家张大兵赴学术会议途中遭遇车祸……网友翻出近五年至少八起类似事件,质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科学家?”

这些事故中受害者多为骑车或乘普通车辆出行的中老年学者。
与此之相反的是,娱乐明星出行常配备专业安保团队。
有评论尖锐指出:“我们愿意为明星的演唱会门票买单,却让科学家的安全‘裸奔’。”

“修医生让我女儿能穿着裙子去上学,而他自己却倒在自行车道上。”
反差刺痛了我们所有人,一个能用显微镜拯救神经的专家,为何救不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引发对高精尖人才安全保护的讨论。




有建议提出,应为重点领域专家配备通勤保障,定制化交通服务或紧急定位装置。
但许多学者养成的低调成习惯,他们许多人常年骑车上下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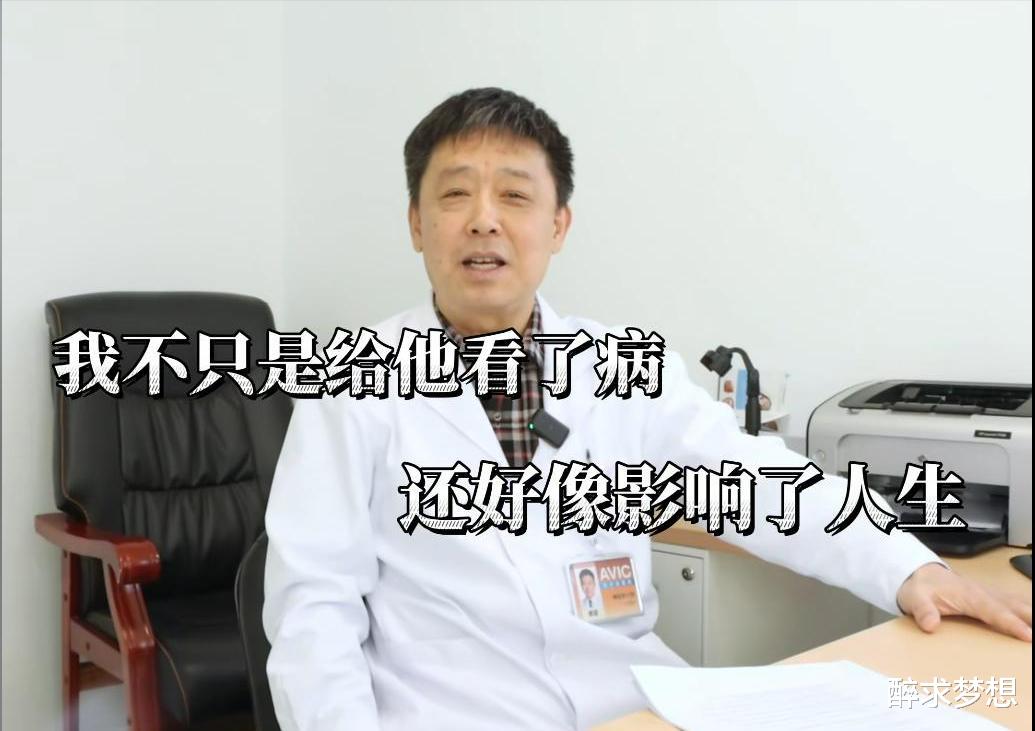
科学家们的安全防线可能脆弱得超乎想象。
当一位顶尖专家修波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他既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也是若干交通事故中一个冰冷的数字。

他的事迹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终结。
他创立的诊疗中心仍在运转,那些被他治愈的孩子正在长大。
最好的悼念,是继续继承他的意志,让这个曾为千万人托起生命希望的人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