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秋的沂蒙山区,鲁中军区二团参谋长刘锡琨伏在冰冷的岩石上,望远镜里清晰映出日军运输队的动向。这支由日军第59师团直属的辎重联队正沿着沂水西岸行进,队伍中42辆大车满载着过冬物资,前后各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护卫。这个情报得来不易——三天前,地下交通员张玉桂扮作疯妇混进日军营地,用浸过米汤的纸条传递出准确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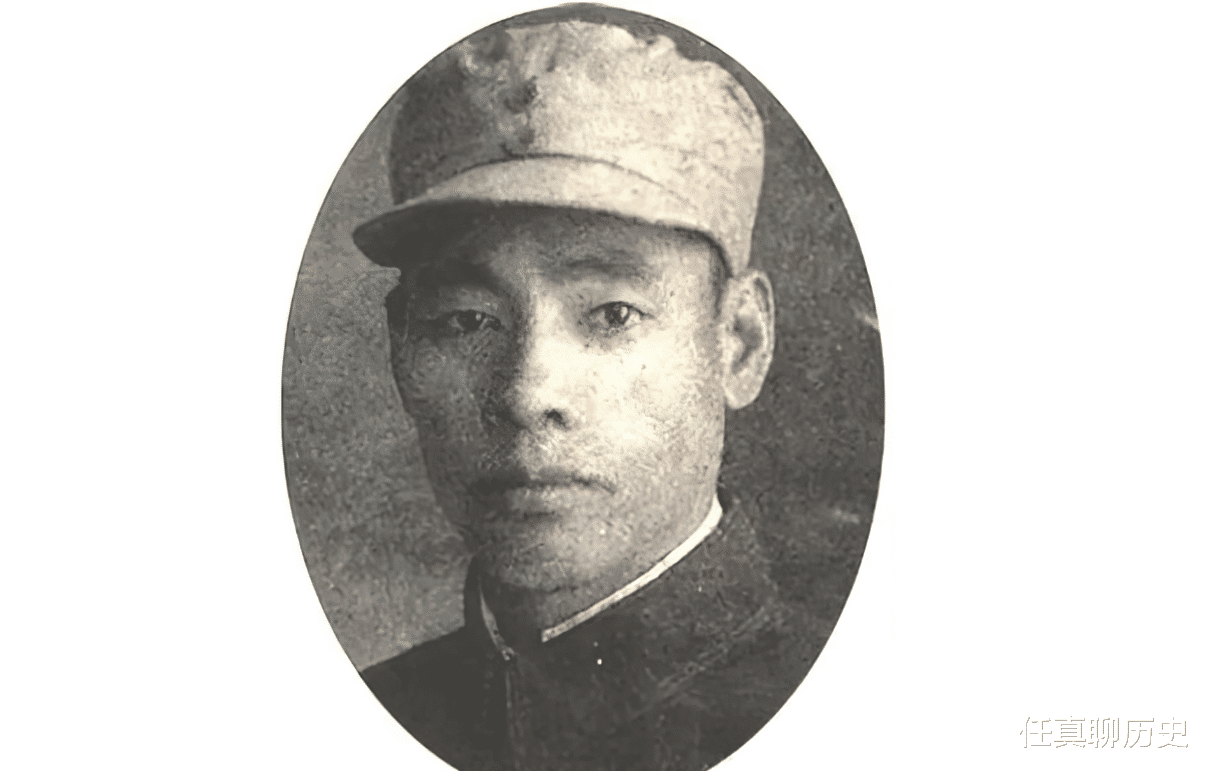
刘锡琨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身旁的警卫员王继成。这个19岁的济南小伙正小心翼翼检查着"黄檀木炮",这是鲁中兵工厂特制的秘密武器:用百年黄檀木挖空内膛,外箍铁圈,填装黑火药与碎铁片,射程虽短但威力惊人。"参谋长,三根炮管都检查过了,火药都是老宋头新配的。"王继成口中的老宋头是兵工厂技师宋澄,这位留日归国的化学专家,此刻正在五里外的山坳里调试最后两门榆木炮。
突然,东南方向传来布谷鸟的啼叫,三长两短。蹲在刺槐树上的观察员李德福立即挥动绑着红布条的树枝——这是日军队列进入伏击圈的信号。刘锡琨摸出怀表,表面玻璃的裂纹记录着上月桃花岭突围时的激战,时针指向下午2时17分。他朝传令兵赵保真比划手势,这个哑巴少年像山猫般蹿向各个埋伏点,三十多名战士屏住呼吸握紧武器,他们中既有老红军出身的机枪手孙大兴,也有刚参军三个月的学生兵陈玉明。
日军指挥官长野荣二少佐骑在枣红马上,军刀随着颠簸轻轻敲击马镫。这位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51期的"中国通"不会想到,前方看似平静的鹰嘴崖即将成为修罗场。当先头部队完全通过第二道标记线时,刘锡琨举起驳壳枪,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际。霎时间,山崖两侧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宋澄带人点燃了埋在岩缝中的火药包,数百斤碎石如暴雨倾泻,将日军队伍拦腰截断。

"打!"随着刘锡琨的怒吼,三根黄檀木炮同时喷出火舌。这种原始武器产生的霰弹风暴瞬间笼罩日军前队,正在组织防御的长野少佐被铁片击中左眼,剧痛中他仍试图指挥机枪反击。但八路军的神枪手们早已锁定目标,孙大兴的捷克式机枪死死压制住日军掷弹筒阵地,陈玉明虽然双手发抖,仍用汉阳造步枪击毙了正在装弹的日军弹药手。
最精彩的战术发生在战斗开始七分钟后。按照预定计划,赵保真带着五名战士突然从侧翼杀出,他们手中的武器让日军目瞪口呆——那是用桐油浸泡过的竹制"火焰喷射器"。这种土造兵器将煤油与硫磺混合物通过竹管喷射,虽然射程不足十米,但熊熊烈火瞬间引燃了辎重车上的棉衣被褥。浓烟中,日军护卫队阵型大乱,王继成趁机带人突入车队,用二十响驳壳枪近距离扫射。
当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倒下时,怀表指针停在3时08分。这场后来被写入鲁中军区战例选编的鹰嘴崖伏击战,共毙敌87人,缴获步枪63支、轻机枪2挺及全部过冬物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锡琨在清理战场时,从长野少佐的公文包里发现了标有"军事机密"的《沂蒙山区扫荡要图》,这份情报让根据地提前转移了三十多个村庄的群众。

战斗结束五天后,在蒙阴县野店村召开的庆功会上,炊事班长周大勇用缴获的日本罐头做了"胜利杂烩"。刘锡琨却悄悄离席,借着月光给妻子齐克写下家书:"昨夜又梦到咱家门前的老槐树,等打跑鬼子,就把埋在树下的那坛女儿红挖出来......"
信未写完,侦查员送来急报:日军正在调集重兵报复。
他收起钢笔,带着尚未散尽硝烟味的队伍,再次消失在沂山七十二崮的迷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