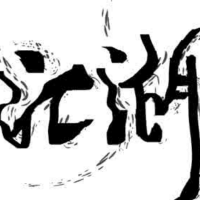1941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名叫玛法的小镇,一位55岁的中年妇女打开了公寓厨房中煤气的阀门,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久,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并在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这些话语虽然只有简短的几百字,但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她的尊严与倔强。

这位走上绝路的女性叫明妮·魏特琳,或许她的离世对美国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在中国,却引起了很大关注。
就在魏特琳去世后,她的在密歇根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葬礼十分简单。但在同一天的中国,南京金陵女大师生在分校校长吴贻芳的主持下,为这位伟大的女士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仪式上,一向坚强的吴贻芳不禁声泪俱下,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一场景。之后,全国人民知道了魏特琳,知道了她光辉且充满遗憾的人生经历。

1886年,魏特琳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西科尔小镇,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贫穷,母亲在她6岁那年不治而亡,从此她开启了凄苦的童年。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性,年幼的魏特琳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顺带帮父亲照看铁匠铺的生意。在这种环境下,魏特琳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
同时,魏特琳非常热爱学习,无论如何繁忙,她也没有放弃学业。上大学时,因家里支付不起学费,她就半工半读,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有名的大学,并获取了硕士学位。

在美国资本主义至上的环境中,信仰成为了穷人们的生活希望,因此,魏特琳也加入了基督教,并以传教士兼教师的身份于1912年来到了中国南京。
靠着自己的高学历,魏特琳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录用,她就是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传奇人生。
入金陵女子大学后,魏特琳先任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有时也担任代理院长,她真诚、有爱、认真、负责,深受学校学生们的喜爱。
同时她坚强、勇敢,在面对即将被日军攻占的南京,她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保护她的学生,保护南京广大妇女。

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魏特琳正在青岛度假。得知消息后的她立刻结束假期返回南京,号召全体师生在校园内挖掘防空壕,进行防空演习,以备战争来临。
此外,魏特琳还与其他教会人士组织了南京基督战时救济委员会,协助将救护车或其他车辆派往空袭轰炸的现场,救护伤员。
随着日军的脚步逐渐逼近,南京市人民十分恐慌,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出成立南京安全区,以便为难民提供保护。

于是,南京各大学校、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公共建筑都被选为难民营地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在安全区的范围之内。
魏特琳立即行动起来,将校园清理安排成难民中心,为妇女、儿童提供庇佑场所,并通知附近街道无法撤离的妇幼,随时可以进入大学内避难。
按照魏特琳的设想,文理学院八栋楼可以容纳2700多人,足够附近居民避难。可她没有想到的是,日军进入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导致大批难民涌入安全区,住所极其紧张。
这种情况下,魏特琳决定,敞开学校大门,接收更多难民。

就这样,在高峰期,校园里收留了一万多名妇女、姑娘,房屋里挤满了难民后,门厅、楼梯上,甚至走廊上、屋顶的回廊里都睡满了人。
魏特琳注意到,一开始涌入学校的难民们情况还算不错,但渐渐地,越来越多受到残暴对待的妇女们出现在学校门口。
魏特琳意识到,外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丧心病狂的日军很有可能会对学校里面的难民下手,而她要做的,是必须保证所有妇女、儿童的安全。此后,魏特琳开始从校园一处奔到另一处,驱赶试图闯入学校的日本人。

至今,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们仍能清晰地记得魏特琳面对日本人的神勇英姿:“她是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手里总是拿着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
魏特琳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挡住了一次次试图闯入的日本人,成为了难民们眼中的“守护神”,可人们不知道的是,每一次的阻挡背后,魏特琳都承受了极大的屈辱。
1937年12月17日,几个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的名义闯进了大学里面,并强制要求魏特琳打开其中一栋住满女难民的大楼。

魏特琳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其目的一定是寻找年轻女子供他们强奸。魏特琳坚决不肯,称:“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中国军人。”几名同行的教师说辞也一致,但这惹恼了日本兵,他们给了魏特琳一记耳光,拿枪抵着她,要求开门。
无奈之下,魏特琳只好开门,日本兵在转了一圈儿后将3个工人绑了起来,称他们就是中国军人。魏特琳坚称:“他们只是花匠,不是军人!”
看到日本人并没有抓妇女,魏特琳心中的忐忑消失了一半,她以为只要自己提供充足的证据,就能将花匠救下来。可她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日军的声东击西,就在她与日本人在前面纠缠的时候,一伙儿日本兵闯入了一栋楼内,掳走了12位年轻姑娘。

此后,魏特琳更加小心,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她依旧不放弃接纳更多的难民。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38年春,随着南京城内的情况慢慢好转,安全区内大多数难民营相继关闭,许多妇女终于敢回家居住。
但也有许多姑娘仍不敢回家,魏特琳也不驱赶她们,而是开设了一个实验中学班,为学龄女孩子们授课,这一项目一直持续到1940年春天。
在南京处在黑暗中的时候,魏特琳就像一束光泼洒在了南京幸存妇女们的心上,她受到了全体妇女们的爱戴。

可就在1940年4月,汪伪政府致使记者在《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污蔑魏特琳的文章。文章称魏特琳是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她曾献出21名妇女给日军。
一时间,魏特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些不知情的人对魏特琳恶语相向。但实际上,文章中所称“魏特琳献出妇女给日军”的事情,实在是她的无奈之举。
那时,日军不顾国际安全区的规定,多次冲进学校欺辱女性,甚至要求魏特琳从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送给日军,不然就要对安全区下手。

魏特琳非常自责,但也无奈答应,可前提是这些妓女必须自愿。最终,有21名妓女被日军带走。这也是《金陵十三钗》的创作原型。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魏特琳无力辩驳,她深受污蔑之词的侵扰,再加上多次亲眼看见妇女们被残忍杀害的场景,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不久就病倒了。
同年5月,在同事们的劝说下,魏特琳决定回国治疗,可在南京经历的事情成了她的心理阴影,使其始终无法释怀,最终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在极度痛苦的病魔折磨下,魏特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在留给世界最后的话语中说道:“我宁愿死去,也不要做个精神错乱的人。”即便死,她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
她还说:“我深深地热爱、崇敬传教事业,可惜我失败了……如果能再生一次,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直到临终前,魏特琳仍心心念念着中国。为此,家人在她墓碑上刻下了“金陵永生”四个大字。
如今,曾经对魏特琳的误解也已解开,她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这是她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