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宋代文坛巨星苏轼的《东坡志林》中,一段令人瞠目的文字将汉代名将卫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段惊世骇俗的评论,竟出自以豁达著称的苏东坡东坡居士之手。
他以“舐痔”(舔痔疮)比喻卫青谄媚汉武帝,甚至将汉武帝如厕时接见卫青的场景,解读为对“奴才”身份的羞辱。
如此刻薄的评价,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卫青为何会被如此评价,我想有以下原因。

出身:从骑奴到将军的逆袭
卫青的崛起堪称草根逆袭的传奇。他本是平阳公主府中的骑奴,因姐姐卫子夫得宠入宫,才进入汉武帝的视野。这一“外戚上位”的标签,成为后世文人攻击的焦点。
苏轼直言卫青“不改奴仆之姿”,认为他“富贵皆因裙带”。然而,卫青初入军营时连战连败的汉军,却在他的改革下脱胎换骨:他首创骑兵奔袭战术,以“迂回包抄”“声东击西”的战略收复河套地区,七战匈奴无一败绩。这样的军事天才,却被文人轻蔑地归因为“天幸”。
武将的“道德困境”
在儒家价值观主导的宋朝,文人推崇“立德”高于“立功”。卫青虽战功赫赫,却被认为缺乏独立人格。
司马迁批评他“以和柔自媚於上”,司马光更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与卫青绑定,称其是“亡秦之失”的帮凶。
苏轼则通过“汲黯对比论”强化这一观点:汲黯直言进谏是“社稷之臣”,卫青顺从君权则是“奴才”。
宋朝文人的集体焦虑
北宋积弱,文人群体对武将的忌惮深入骨髓。狄青因军功升迁却被诬“家犬生角”,最终忧愤而亡;
种师道解汴京之围后反遭贬斥——这种“抑武扬文”的政治生态,投射到历史评价中,便演变为对卫青的贬损。
苏轼的激烈言辞,实则是宋朝文人对自身“以文驭武”权力结构的维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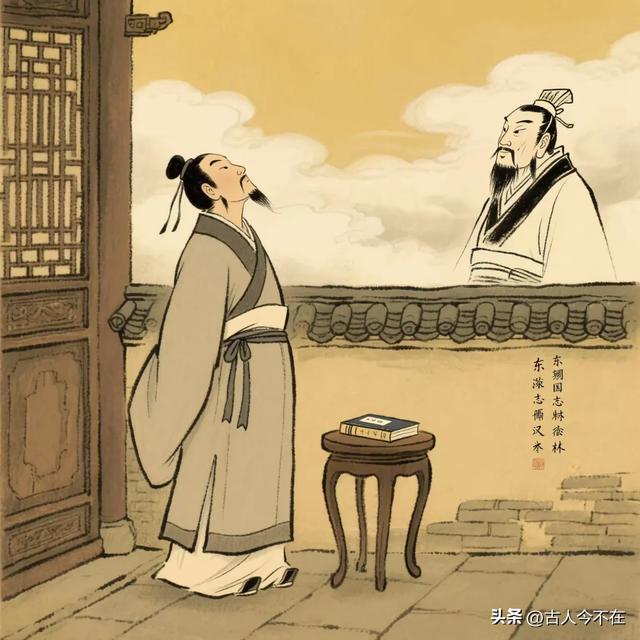
《东坡志林》中的历史暗流
苏轼对卫青的抨击,绝非一时兴起的“键盘侠”行为。在《东坡志林》中,他借古讽今的意图昭然若揭:
对皇权的隐晦批判:将汉武帝刻画为“无道之君”,实为暗讽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导致朝堂动荡。
文人的“道德优越感”:苏轼以汲黯自比,塑造“直臣”形象,既是对自身政治失意的宣泄,也是对“武将威胁文官话语权”的警惕。
历史书写的权力博弈:宋代文人通过重构卫青的形象,将“武将必须依附文官道德体系”的观念植入历史叙事,以此巩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

剥开文人建构的层层迷雾,真实的卫青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军事革新者:他打破中原王朝对匈奴的被动防御,首创骑兵集群作战体系,被李靖、岳飞等后世名将奉为“战法革新第一人”。
政治智慧:位极人臣却谨守君臣之礼,面对李敢行刺选择隐忍,避免引发朝局动荡。
人格魅力:司马迁虽对其有偏见,仍承认他“仁善退让”,与士卒同甘共苦,赏赐尽分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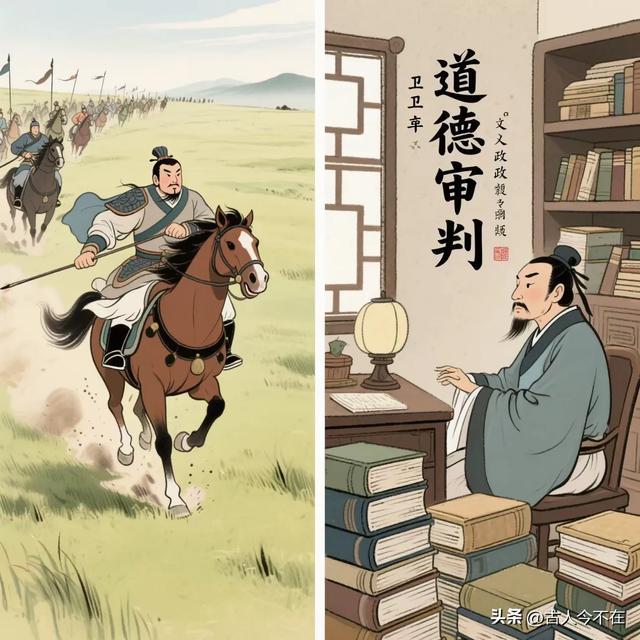
苏轼与卫青的“恩怨”,本质是两种文明逻辑的碰撞:
草原与中原的对抗:卫青的骑兵战术代表着农耕文明对游牧力量的首次系统性胜利,而宋朝文人却因自身武力衰退,将这种开拓精神污名化为“穷兵黩武”。
文人政治的悖论:宋代士大夫以“道德审判”消解武将的历史贡献,却在靖康之变中暴露出“空谈误国”的致命缺陷。当金兵将宋朝后妃“折价充贡”时,苏轼笔下“舐痔”的屈辱竟成现实。

苏轼的“毒舌”与卫青的“原罪”,映照出历史书写的复杂性与权力性。今天重审这段公案,并非要为卫青翻案或否定苏轼的文学成就,而是揭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当文人垄断历史解释权时,武将的功绩该如何被铭记?
或许正如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在民族生存的危机时刻,那些被文人唾骂的“武夫”,恰恰是文明存续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