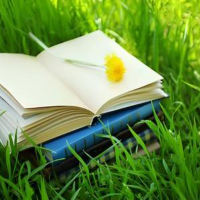金日成借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国内派”和“苏联派”这两大势力给解决了。这时候,他在朝鲜想要独揽大权,就只剩下一个绊脚石了,那就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延安派”。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朝鲜有个延安派,他们跟其他两个没啥后台的派系可不一样。这个派系在朝鲜政坛里,那可是相当有分量,手握大权。
与此同时,那44万志愿军在停战后留在朝鲜,就像是朝鲜“延安派”手里的一张秘密王牌。
“国内派”和“苏联派”都落魄后,“延安派”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金日成迟早会对他们动手。朝鲜战争一打完,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可这些筹划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这场政变不光没能让“游击队派”垮台,反而还帮金日成一把,让他顺利坐上了权力的头把交椅。
【延安派】
上次我跟大家聊了聊,建国那会儿朝鲜政坛里头分了四大帮派。不过啊,这四大帮派的力量可没那么均衡。

1946年8月份,北朝鲜劳动党搞了个成立大会,会上不光是把36万6千多名党员给正式认定了,
选举结果出炉,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一共有43位当选。金日成原来的游击队一派只拿到了5个位置。而延安派作为实力最强的一派,占据了优势,他们总共得到了19个席位。更让人瞩目的是,前延安朝鲜军政学校的校长金枓奉,他还被大家选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
不过,延安派人数虽多,却一直没能找出一个像金日成那样的领头人。没有个核心人物,这就成了金日成削弱延安派的一个好机会。
朝鲜战争一开打,金日成就瞅准了时机。他瞅见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头阵吃了亏,就把战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推给了那些不同路子的人。那时候,朝鲜急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头儿,所以中苏两边对金日成在打仗那会儿搞的小圈子、拉帮结派的事儿,大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咋去管。
在中苏的默许加上对手内部不和的情况下,金日成不光巧妙地把延安派的朴一禹等人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而且在战争快结束时,干脆彻底解决了那些已被排挤到边缘的“国内派”。
【主体思想】
朝鲜战争打完后,金日成在朝鲜里头那就算是站稳了脚跟,地位无人能及。不过呢,这种老大的位置吧,明面上没说破,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键原因是,为了跟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较量,苏联不光得自己摆脱独裁的标签,还得管着它的小弟们,不让它们变成让人瞧不上的独裁政权。
1956年2月份,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会议上,搞了个内部讲话,主题叫做《谈谈个人迷信以及它惹出的事儿》。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大伙儿看到苏联正在往好的方向走。
那个秘密报告一出来,红色阵营里头可炸了锅。但在离莫斯科老远老远的平壤,金日成却觉得这是个机会。在朝鲜,就金日成一个人看出,赫鲁晓夫这是在拿自己的地位下注,玩一把大的。
朝鲜战争打完后,金日成就成了大家心里的大英雄,被崇拜了整整四年。不过,老百姓对他那种没头没脑的追捧,也让朝鲜高层里不少人对他有了意见。
不少人都说,他故意拿“个人崇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事儿金日成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瞅着那些不满他的人,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聚到一块儿。
不过,苏共二十大的那份报告,不光是把斯大林那时候的个人崇拜问题给抖搂出来了,还顺带给金日成送了个台阶下,毕竟他那时候也真在搞“个人崇拜”那一套。

他一开始就说,苏联那份报告说得一点没错,接着他很干脆地承认,朝鲜国内也确实存在对个人过度崇拜的问题。
不过,由于苏联也曾遭遇类似情形,金日成指出,个人崇拜的问题源于部分苏联派人员的误导性宣传。随后他又说明,个人崇拜其实被夸大了,很多人错误地将民众对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和信任解读为个人崇拜。
金日成抓住这个机会,说:“咱们得把好的民族文化传统传下去,还要让它跟马列主义一块儿发光发热。”
这个说法是金日成提出的“主体道路”,它后来发展成了“主体理论”的基础。尽管金日成的这条主体道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点,跟传统的马列主义差别挺大。
苏共二十大之后,朝鲜推行了一条新的道路——主体路线,这条路线迅速赢得了众多朝鲜干部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崭露头角的新晋干部们,他们成为了这条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他们支持主体思想有清晰的缘由,这批新来的干部不属于以前的四个老派别,要想往上爬,就只能在这四个派别里找到靠山。
有了这批人的支持,金日成不仅没陷入个人崇拜的泥潭,还迅速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他倡导的“主体路线”上。

赫鲁晓夫那份隐秘的报告,让共产主义大家庭里起了纷争,特别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看法有了分歧。这样一来,中苏两边都忙得不可开交,暂时没心思去管朝鲜那边的事情了。
金日成表面上退隐,实际上却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这让他的个人崇拜愈发根深蒂固。那些原本就对金日成心存戒备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残余成员,心里头更加明白,要是再不采取行动反抗,
等那些新干部逐渐成熟起来,在金日成面前,他们根本没法反抗。所以,这批人就开始拼死一搏,而这一搏,就成了大家说的“八月事件”。
【八月事件】
朝鲜战争打完后,志愿军没立马全走。到了1956年年初,还有44万志愿军留在朝鲜呢。他们不光是为了防着美国再来捣乱,帮朝鲜看着点儿,还使劲儿帮朝鲜搞国内建设,帮了大忙了。

从1953年到1956年那会儿,志愿军可没少帮朝鲜老百姓。他们帮忙把地给整平了,让大家能重新种上庄稼。不仅如此,他们还建起了好多房子,加一块儿面积超过了23万平米。另外,那些被毁的大小桥梁,他们也给修好了,数量超过1300座。
不过,金日成确实感激志愿军对朝鲜经济复苏出的力,但他心里也明白,中国有个规矩,就是不管别国内政。所以,他压根儿没觉得志愿军会挡着他集权的路。
另一边,金枓奉带领的反金一派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所以,在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会儿,他们就在中央全会上,下定决心要罢免金日成。
他们让当时的朝鲜商务大臣尹公钦站出来,直接批评金日成过分推崇个人崇拜。尹公钦原本以为,自己说的是实话,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他万万没想到,现场的大部分人,要么是金日成的铁杆追随者,要么就已经被金日成给拉拢过去了。
改革派刚开口没多久,就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孤掌难鸣。会议刚收尾,尹公钦带头的那些反对金日成的人,没动武也没开枪,立马就开始琢磨怎么离开朝鲜了。

在那个时刻,金日成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关键的一个抉择,那就是暗中不作声,让反对派就这么溜出了朝鲜。
金日成心里明白,在国内加强自己的掌控力其实不算啥大问题。可要是反对他的人开始搞动作,这事儿要是让中苏两国知道了,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
就像金日成预料的那样,尹公钦一看情况不对劲,当天就从平壤溜了,没过几天就跑到了北京。尹公钦到北京后,哭着跟中国说了朝鲜那边的事儿。中国对具体情况还不太摸底,所以没直接找朝鲜的麻烦,而是先去问了问苏联的看法。
苏联虽然之前听说过有些反对的声音,但对于朝鲜内部到底发生了啥,还有金日成本人到底怎么想的,其实并不太清楚。
八月份那事儿过了才二十来天,米高扬和彭德怀带着的中苏团队就到了朝鲜,他们直接去找金日成了解情况。谈话间,他们隐晦地提到,要是情况不妙,大家可能会联手采取行动,不过这话没明说是针对金日成的。
金日成其实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局面,他表面上装作挺为难的样子,但实际上却爽快地答应了大部分要求,比如让反对派的人官复原职,还有不进行大规模清洗等等。

金日成那会儿及时低头,给中苏挽回了颜面。但他这么做,其实就是想拖时间,等机会。八月那事儿在朝鲜国内可炸了锅,之前藏着掖着的矛盾,全给摆到明面上了。那事儿过后,金日成和那些反对他的人,那是彻底对立开了。
中苏代表团离开后,金日成开始对反对派动手脚,暗中给他们制造麻烦。等中苏那边因为匈牙利事件忙得不可开交时,金日成立马抓住机会,把所有反对派都抓了起来,一个不落。
延安时期的老前辈金枓奉,快八十岁的时候,被悄悄关了起来,大概在1960年前后离世。而另一位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崔昌益,则是被公开逮捕,最后在监狱里没了性命。
八月那档子事儿,让金日成的那些最后的反对者们自己走上了绝路。而那些老早就跟着金日成混的旧派,其实也没捞到什么好果子吃。
朝鲜战争结束后,有个叫金昌满的延安派成员活了下来。他虽然一开始是延安派的,但很早就开始跟金日成拉近关系,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到了那个八月事件,他还成了中国不插手朝鲜事务的重要人物。

不过金昌满的结果并不好,八月事件过后,他虽短暂地坐上了朝鲜副首相的位置,是在金日成的手下。但好景不长,没多久他的所有官职就都被拿掉了,从此在朝鲜政坛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金日成能够一步步清除国内的政治对手,主要靠的是他巧妙地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全球形势的精准把握。不过,虽然他在政治上相当有头脑,但最终还是坚持要把权力交到自家后代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