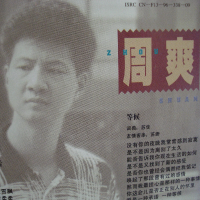首先声明,我不是标题党,哪怕是“欲盖弥彰”。
看过一部电影“万箭穿心”。我这个中年人也会对号入座。电影里的主人公,被生活折磨的杂乱无章,被生活撩拨得欲罢不能,最后归罪于应该是房子的风水不好,不堪重负,杀身成仁。说实话,虽然看电影的人不多,但我走出电影院的脚步是沉重的,好像很多地方我都中标了,比如房屋的对面有光射过来,我会上门礼貌的告诉对方,我忌讳。
“万箭穿心”让我有了后遗症,沉重的脚步伴随了我几个星期,我甚至怀疑我是否得了抑郁症,电影的作者是方方,一个我喜欢的作家,看过她很多的小说,成名作“大篷车上”还被改版成电视剧,现在已经大腹便便的酒窝男毛永明主演,那个年代是光荣属于新一辈的八十年代,是中国正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又热火朝天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情怀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大师和灯塔的年代,而我崇拜的大师们:池莉,黄蓓佳,方方,张抗抗。
方方,写实派的作家,她用文字和广大的读者一拍即合,瞬间迸发出共鸣,因为大家就是这样生活着的,但凡,写实派的作家都有一个通病,只认本实描写,不闻价值判断,把市井小民,生活不易,甚至无可奈何的绝望中一种自我麻醉的安慰等等无水分的和盘托出,毫无风雅可言,至于价值,社会价值的判断通通交给读者去自我消化。
需知作家是有社会责任的,而寻常百姓的可贵,朴实的价值观随处可见,既有用骨头里挣的钱做得的红烧肉才能吃得心安理得的一根筋,也有穷的叮当响却充满爱心的清洁工,经常会看到呵护农民工的新闻,建设鸟巢的农民工那笑容有多灿烂,正面的呵护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坚强的躯体,无惧电闪雷鸣,虽然已经遍体鳞伤,但还是冷面相对,如果你拿出一点点的关怀,他会瞬间解体,泪流满面,从此改变三观,没有仇恨。
世俗一定有偏见,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即使面对“倚门之娼,“江湖之盗”,也要有挽救之心而不是铺天盖地的鞑伐。方方是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点毋庸置疑,她的作品无论是白字三部曲,还是桃花灿烂以及描写知识分子的行云流水等等都能看到她自己的影子,尤其到现在我还恋恋不忘小说里的人物“小八子”。最欣赏她对凡俗人生的主题升华,恰似透明试的人性描写,她的小说能够棋高一招就在于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大段具有原生态细节的描写,这是作家对读者的尊重。九十年代初,我猫在深圳,海南的出租屋里,方方的小说就是我的午餐,喜欢,超级喜欢,我是她的粉丝。
但是面对冠状病毒,她的方向倾斜了,“方方日记”是一部让我沉重的日记,一部告诉你天塌下来的日记,一部真实性她自己也搞不清或者灯下黑,铺满血滴子的日记,她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就像邻居家着火了,水和桶就在手边,大家惊慌失措的忙忙碌碌的时候,她却哭哭啼啼不停的叨叨叨叨,喋喋不休,殊不知把桶装满水泼向火焰是这个时候最准确的做法。有一篇日记,她引用了排比文字,怎么看都像一篇檄文,我看着她的日记心里却想着:别添乱了,求求你了。
武汉已经解封了,我在头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在武汉等你”。终于,又可以领略晴川阁与黄鹤楼夹江相望的伟岸深情,伯姓牙名的古琴台,籁音缭绕在春雨之后的天空上,长春观”射雕英雄传里全真教七子丘处机正在书写:“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武汉大学的樱花依依惜别着美丽的春色,阅马场的暮鼓,敲响的是一帘寒梦之后的阳光,归元禅寺的钟声远了又近,近了又远。
枝江大曲的开启,武昌鱼的朵颐映射着全国支援武汉的光辉,那些逆行者们微笑着告诉病患,她们不是逆行,而是专程。多么好的姑娘们,她们已经成为了武汉的女儿,方方也说,她是武汉的女儿,是中国的作家,此刻,她的日记显得多么苍白。